《想象的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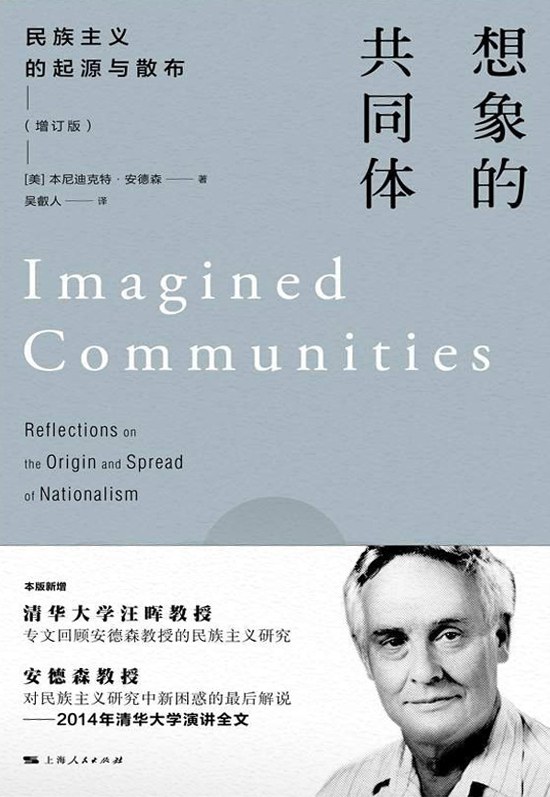
短评
几乎需要全文背诵的经典,不专属于任何学科跨学科专著,同时有文学般精美凝练的文字。
本书的著名观点:民族是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同时也是最大的误解,这不代表民族主义是一种虚假人为的产物,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新的、被创造的社会事实,是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
一、“民族”产生的两大先决条件:1.认识论。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引发的新的共同体的想象。2.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三者的重合。
二、四波民族主义:1.美洲模式;2.欧洲群众民族主义;3.欧洲官方民族主义;4.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
三、殖民地政府通过人口调查、地图与博物馆三种制度塑造了殖民地民族的自我想象。民族历史叙述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
笔记
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老问题与新困惑——汪晖
《想象的共同体》最著名的观点是: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即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
他们两人(安德森和厄内斯特·盖尔纳)也都指出这种想象的、创造性的方面并不等同于说民族主义是一种虚假的、人为的产物,而是一种新的、被创造的社会事实。这些观点明显受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社会理论、心理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
不同于那些认为民族主义是从欧洲漫延至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观点,他认为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是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或称远程民族主义。这一民族主义综合了殖民地各阶层的诉求,反抗宗主国的压迫和不平等对待,但在价值上同时汲取了欧洲启蒙思想。这种对于新的政治共同体的想象是那些去往宗主国的“克里奥尔”官员和当地“克里奥尔”印刷工的创造物。
《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研究的贡献或许可以被归纳为如下几点:首先,它不是用族群、宗教、语言等社会要素解释民族形成,也不是用工业化或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说明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是别有新意地提出印刷资本主义与新的政治共同体形成之间的伴生关系。这为民族形成是一种现代创造过程或想象过程的论点提供了前提,也为颠倒传统观念中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衍生关系铺平了道路,即不是民族产生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其次,历来的民族主义研究都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原则和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视为一种向全球扩展的体系,并以此为主要视角分析非西方地区的民族主义,而安德森却倒置了民族主义的历史,即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欧洲的产物,恰恰相反,最早的民族主义是发生在北美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即一种远程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最早的民族主义是殖民主义全球关系的产物。
- 印刷资本主义与新的政治共同体的伴生关系(不是民族产生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 民族主义不是以欧洲为中心向外扩散的产物,而是最早发生在北美的“远程民族主义”。
他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用一种对于非西方读者难以理解的方式讨论弥赛亚时间与民族主义的空洞、均质的时间之间的关系。
他在清华的演讲却以极为浅显的方式再度通过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展开对民族共同体特征的描述:民族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都涉及信念和情感,但两者的区别是什么?人们像认同宗教一样相信自己的国家是好的,却不会像宗教信徒相信上帝绝对正确那样相信国家的完美。民族主义的情感表述是:即便我的国家会犯错,但在情感上,不论国家对错,她依旧是我的国家。这与宗教共同体的信念产生了区别:民族和民族领袖可能犯错,而宗教——如同大多数欧美理论家们一样,安德森的宗教论述基本上是在一神教的范围内——不会承认信仰和上帝会犯错。这种信念形态的区分其实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世俗信仰与超越信仰之间的区分,即国家——以及他的贤明的或犯错的先人——始终与我们同在,他们既不上天堂也不下地域,是现世的或历史性的存在(故而可以犯错),而上帝却在天堂里,他永远正确。
正如民族主义运动或民族主义领袖一再诉诸家庭、家族、宗族等等血缘共同体以表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纽带,安德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了民族认同与亲缘纽带在情感特征方面的联系和区别。他比较孩子对母亲行为的羞耻感与民族感情中对于民族行为或状态的羞耻感,不但说明了民族认同对亲缘关系的模拟,而且也以此论证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区别。
听到安德森对于羞耻感的讨论,我禁不住联想起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有关原罪与羞耻的讨论,即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一种罪感的文化,而日本或东亚是耻感的文化,前者源自超越的视角,是真正个人主义的,而后者却是在他者注视下的情感方式,是共同体伦理的产物。
本尼迪克特与安德森都没有将羞耻感历史化,即有意或无意地遮盖了羞耻感总是在某个他者的注视之下才能发生,羞耻感是历史性权力关系的产物。在欧美之外的地区,除了西方或内在化了的“西方”,还有谁能够拥有让人羞耻的目光呢?如果从摆脱羞耻感的角度去观察亚非地区的民族革命,除了让那个目光感到满意之外,我们该从哪里去发现其创造性和自主性?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这一概念(远程民族主义)用于对于18-19 世纪美洲民族主义的探讨,其形成的基础条件包括:①移民群体、②远离母国、③与母国的亲缘关系、④殖民地与宗主国的政治关系(认同与反抗)、⑤大规模移民得以可能的航运技术和印刷资本主义的诞生,以及⑥由这些基础条件而产生出的情感特征。如果说前三项是所有移民群体共同具备的条件,那么,后三项却因时、因地而发生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移民群体会转化为新的民族,而另一些移民群体——即便在没有完全同化于当地社群的条件下——却逐渐疏离于对母国的认同,其族裔认同始终不会上升为独立的民族认同。
换句话说,移民及移民群体的形成并不必然产生远程民族主义,若无其他政治条件,族裔认同或地方认同将无法上升为民族认同,族裔或地方性共同体也因此不可能上升为政治共同体,亦即民族。这也从相反的方向,说明了民族主义与民族的关系,即如果没有一种有力的民族主义,即便存在语言、宗教(文化)和族群等社会要素,民族也不可能形成。
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吴叡人
卡欣是美国印尼研究的先驱,“康乃尔现代印尼研究计划” ( 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 的创始人。他聚集了一批顶尖的人才到康乃尔,使这所大学成为美国东南亚研究的重镇,至今仍声誉不衰。
通过研读印尼文学,特别是伟大的印尼小说家普拉莫底亚·阿南达·托尔 (Pramoedya Ananta Toer ) 的作品,他开始注意到文学如何可能和“政治的想象” (political imagination ) 发生关联,以及这个关联中蕴涵的丰富的理论可能。
在安德森眼中,“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问题构成了支配 20 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缺陷。
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 ( modern ) 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 ( modernity ) 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使这种想象成为可能的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
首先是认识论上的先决条件 ( epistemological precondition ) ,亦即中世纪以来“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的变化”。这种人类意识的变化表现在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只有这三者构成的“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旧世界观在人类心灵中丧失了霸权地位,人们才有可能开始想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共同体。安德森借用沃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 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 ( homogenous, empty time ) 概念来描述新的时间观,并指出 18 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 (re-presenting ) 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因为它们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
但与过去在认识论上的决裂本身不足以说明在诸多可能类型的“水平-世俗”共同体中,为何“民族”会脱颖而出。要“想象民族”,还需要另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而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形成的特殊主义的方言—世俗语言共同体,就是后来“民族”的原型。
认识论与社会结构上的条件,酝酿了民族共同体的原型,也为现代民族搭好了舞台。以这两个共同的基本先决条件为论证出发点,安德森接着一步一步地建构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如何从美洲最先发生,再一波一波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散的历史过程的扩散式论证 ( diffusionist argument ) ——一种前后关联,但每一波都必须另作独立解释的复杂论证。
- 认识论。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引发的新的共同体的想象。
旧世界观: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
新世界观: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 - 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三者的重合。
“第一波”所创造的“美洲模式”,是一种不以语言为要素的民族主义;然而受到“美洲模式”感染与启发而在 1820 年以后出现于欧洲的“第二波”民族主义,却是一种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
安德森特别提出了“盗版” ( piration ) ——自觉的模仿——的概念来衔接先后出现的民族主义:作为“第二波”,19 世纪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因为已有先前美洲与法国的独立民族国家的模型可供“盗版”,因此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比“第一波”要更有自觉意识。
“第二波”民族主义在欧洲掀起的滔天巨浪,撞击统治阶级古堡高耸的石墙后所反弹涌现的,就是“第三波”的民族主义——也就是 19 世纪中叶以降在欧洲内部出现的所谓“官方民族主义” ( official nationalism ) 。安德森指出,“官方民族主义”其实是欧洲各王室对第二波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无力抵挡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旧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被群众力量颠覆,于是干脆收编民族主义原则,并使之与旧的“王朝”原则结合的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先期 ( anticipatory ) 策略。
如果“第三波”的“官方民族主义”是对第二波的群众民族主义的反动与模仿,那么“最后一波”,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则是对“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帝国主义——的反应,以及对先前百年间先后出现的三波民族主义经验的模仿与“盗版”。
- 美洲模式:不以语言为要素的民族主义。
- 欧洲:群众民族主义,对美洲模式的自觉模仿(盗版)。
- 欧洲:官方民族主义:源自俄罗斯化政策,是对第二波的反动与模仿。
- 最后一波: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对“官方民族主义”另一面“帝国主义”的反应。
在 1991 年出版的修订版《想象的共同体》当中,安德森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又收录了两章具有附录性质的论文。他在“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一章中提出了一个布迪厄式( Bourdieuian ) 论证,试图补充修正第七章(“最后一波”)关于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解释。他指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并非 19 世纪欧洲王朝国家,而是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他举出三种制度(人口调查、地图与博物馆)说明殖民地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化 ( institutionalization ) 和符码化 ( codification ) 的过程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转移到殖民地人民身上,并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想象。在“记忆与遗忘”一章中,他则探究了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指出民族历史的“叙述” ( narrative ) 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
- 三种制度(人口调查、地图与博物馆)。殖民地政府通过制度化和符码化的过程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转移到殖民地人民身上,并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想象。
- 记忆与遗忘。论述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民族历史的“叙述” 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和已故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 ( Ernest Gellner ) 所写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 这两本同样在1983 年出版的著作如今已是民族主义研究最重要的两本经典之作了。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提出的那个标准社会学式的结构功能论论证,无疑已为侧重实证主义的主流社会科学开出了一条建构民族主义的一般性理论之道。
安德森在相对简短的篇幅内就建构出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般性历史论证。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方法是研究民族主义最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因为几乎所有民族主义的现象都同时涉及了历史纵深(如特定认同形成过程)以及跨国因素(如帝国主义扩张)。然而这个研究途径的“操作”非常困难——研究者必须有能力在历史的精确性 ( accuracy ) 与理论的简约性 (parsimony ) 之间取得平衡,并且要有非常杰出的叙事 ( narrative ) 技巧。
他和兄弟佩里一样擅长运用既有历史研究的成果,并将之与理论性概念结合,然后以惊人的叙事能力,编织成一个同时观照古今东西的“历史类型”或“因果论证”的文本——谁说社会科学家不需要文学素养和文字能力?
第二,安德森超越一般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的表层观点,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他将民族主义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脉络当中来理解——民族主义因此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或者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种“文化的人造物”)。这种
第三,《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结合了多重的研究途径,同时兼顾文化与政治、意识与结构,开创了丰富的研究可能性,因此被北欧学者斯坦·东尼生 ( Stein Tonnesson )和汉斯·安德洛夫 ( Hams Antlov ) 称为“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途径的桥梁”。就传统比较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它关于民族主义的各种“历史类型”以及“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构与制度条件”的论证。
印度裔的美籍中国史专家,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 教授也以中国史为证提出一个与此论战相关的经验批评。杜赞奇认为,早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对中国而言,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
安德森虽然认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
延伸阅读
哲学
瓦尔特·本雅明 “同质的、空洞的时间”(homogenous, empty time)
社会学
皮埃尔·布迪厄
《民族与民族主义》
《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
文学
《人世间》《万国之子》《足迹》《玻璃屋》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布鲁岛四部曲
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