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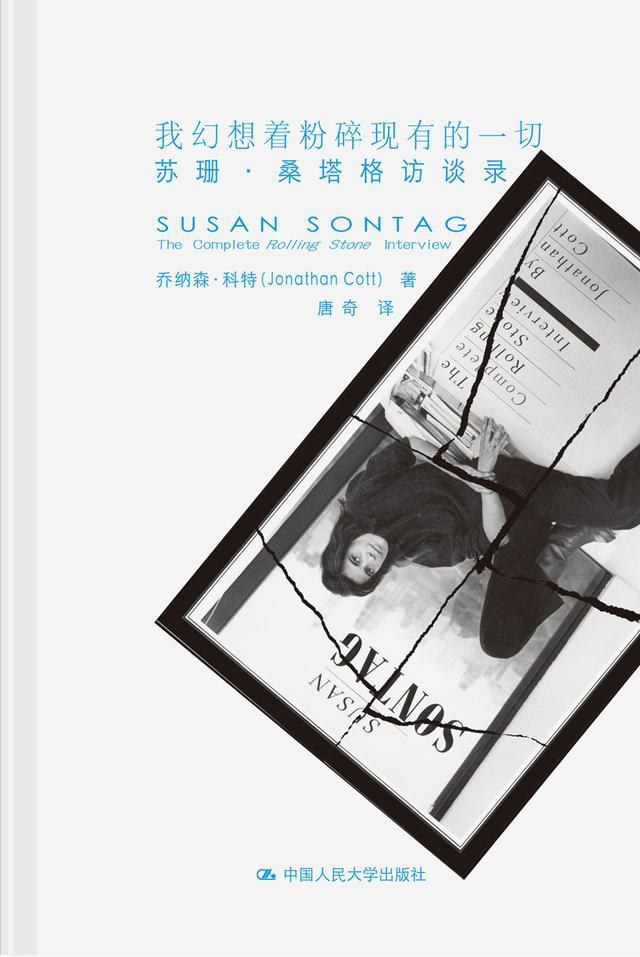
-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乔纳森·科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读完:2022-12,评分:8/10
短评
笔记
引言
当一个人死去,我们就失去了一座图书馆。
——古代基库尤(Kikuyu)谚语
序
“你说我们现在和曾经有过的一切都归功于文学。如果书籍消失了,历史就会化为乌有,人类也就会灭亡。我确信你是正确的。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独断总结,它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有的人认为读书只是一种逃避,即从‘现实’生活的每一天逃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书籍的世界。书籍不单单是这样的。它们是使人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
——《给博尔赫斯的一封信》,1996
疾病的隐喻
我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和痛苦的手术,还有我所有的思想都将在一两年之内死去的事实。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还有害怕和恐惧,我吓坏了。我经历了不折不扣的动物性的恐慌,但是也经历了无与伦比的狂喜。我觉得似乎有一些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似乎我正要投入一次伟大的冒险——生病和可能死亡的冒险,而愿意迎接死亡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由于宗教信仰的消失,精神价值只能依附于两件东西:艺术和疾病。
我总是尽我所能地承担责任。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讨厌把自己当成受害者,那不仅让我不愉快,甚至让我寝食难安。在可能的范围内,只要不太极端,我的自主意识总是不断膨胀,所以在友谊和爱情中,我总是迫切地为一切好事和坏事负责。我不喜欢这样的态度:“我本来好得很,都是那个人害了我。”即便有时候事实的确如此,我也会努力说服自己,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坏事至少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这让我感觉更有力量,让我相信自己有可能改变现状。所以我对这种信念抱有很多同情。
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种混淆视听的观念,把人们从他们真正应该负责的领域支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所有这些思维方式都是反智的,疾病的心理学理论的大部分拥趸都不相信科学。
有一个隐喻我在书中没有提到。到了现代,原本归结于结核病的东西一分为二——积极、浪漫的一面给了精神疾病,消极的一面给了癌症。但是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隐喻,跟结核病一样耐人寻味,那就是梅毒,因为梅毒也有积极的一面。梅毒不仅因为跟滥交有关而充满罪恶感、令人生畏和富于教化意义,而且附带有精神疾病的属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结核病与其分化之间缺失的一环:一方面是精神疾病,另一方面是癌症。
(梅毒)就像是生命忽然间加速了。因为这些表现被认为是梅毒患者的典型症状。你可以在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中看到,梅毒被认为是天才的代价,它被赋予了某些原来归结于结核病的特质。当然,梅毒会带来疯狂、痛苦和最后的死亡,但是在开始和结束之间,一些了不起的事发生了。你的头脑迸发火花,产生了天才的想法。尼采、莫泊桑这些梅毒患者都死于梅毒。但是他们都有过那种狂热的精神状态,疾病是他们天才的一部分,或者说疾病造就了他们的天才。所以梅毒作为一种天才的疾病有其浪漫的一面,在你陷入彻底疯狂之前,给你十几二十年心理活动最剧烈、最亢奋的时间。
白血病是癌症的隐喻中唯一具有浪漫色彩的。如果说有哪种癌症可以成为一种浪漫的疾病,那就是白血病。
白血病是浪漫的癌症。或许因为它是一种与肿瘤无关的癌症,血液中不可能长出肿瘤。白血病给人的感觉不是你的体内长出了什么东西,而是你体内的某种东西正在生长,因为白血病让你的白细胞从20亿增加到90亿。细胞在增殖,但是不形成肿瘤,你也不能做手术摘除它,癌症令人恐惧的截肢和器官切除都不会发生。
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
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重要因素就是看它是否允许人们成为边缘人。 而有些国家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思想中容不下愤世嫉俗者或边缘人。在我看来,无论如何,任何时候人们都应该有坐在路边的自由,过去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许多人选择成为边缘人,而其他人并不介意。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接纳边缘人和边缘意识形态,而且要接纳不寻常和异端。我就是个异端。当然,我还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异端,虽然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中庸之道。
我相信历史,现在人们不再相信历史了。我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都是历史的产物。我的信仰很少,不过这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我们认为自然而然的事物大多有其历史根源——特别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谓的浪漫主义革命时期——我们今天的许多期望和感受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比如关于幸福、个性、激进社会变革和快乐的观念。我们使用的很多词汇都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诞生的。
关于50年代人们有许多愚蠢的言论,不过喜欢流行文化的人与喜欢高雅文化的人之间的确是完全隔绝的。我从来没见过对二者都感兴趣的人,而我自己一向如此,所以我习惯了什么事情都自力更生,因为我没办法与人分享。当然,后来一切都变了。这正是60年代的有趣之处。
Q:我觉得威尔海姆·赖希在谈到如果法西斯主义攫取了这种破坏性冲动会怎样时,表达了一种跟你不同的性观点。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利用了受压抑的性欲带来的挫折感,在我看来,你会说因为人类的性器官从根本上就是病态的,所以法西斯主义可以轻易地利用它。但我想赖希会争辩说,它之所以能够被利用,是因为事实上它是健康的,只是找不到一种健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A:我也相信是这样。我知道有些人的性生活是愉快、享受、没有破坏性和虐待倾向的。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不可能。事实上,那不仅可能,而且很值得期待。只不过我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没有走到极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他们也不应该走到极端。但是我不同意赖希关于法西斯主义主要来源于性压抑的观点,尽管我承认其中一些性言论对人们很有吸引力。
Q:你曾经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纳粹标志的流行实际上不是对一个人个性的肯定,而是对“被压抑的性选择的自由”达到了“个人无法忍受的程度”的反应。
A:是的,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朋克现象。人们知道我喜欢去听摇滚音乐会,他们总是问我怎么能那样做,特别是因为纳粹标志。但我不认为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只是在虚无主义的背景下一种强烈愿望的表达。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虚无主义基础上的——电视就是虚无主义。我的意思是,虚无主义不是什么先锋派艺术家的现代发明。它就存在于我们文化的核心之中。
论摄影
生命不是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被一道闪光照亮,永远地凝固。照片却是。
论风格
在现代派、先锋派、实验派或者其他我心目中的优秀作品中,很多让我感兴趣的东西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隐喻的净化。这种朴素是贝克特和卡夫卡吸引我的地方。我过去很欣赏罗伯·格里耶那样的法国小说家,现在没那么欣赏了,他们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不使用任何隐喻。
写作与阅读
两年前我重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跟我十几岁第一次读时一模一样,或许更深刻了。我是说,这是最惊心动魄、最振奋人心、最激昂、最高尚的作品……读完这本书的几个星期里我的感觉就像在飞翔。我想:真不可思议,现在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了!我有这么多年没有读它,而我的感觉还跟17岁第一次读它的时候一模一样。我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你可以在任何年龄阅读,而且总是可以有所收获的作品。不过,像《红与黑》和《金碗》,就是适合成年人阅读的作品。
我在写作《疾病的隐喻》时不需要经常查阅文献,因为我记得《伊利亚特》第二卷的瘟疫、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瘟疫、薄伽丘笔下的佛罗伦萨瘟疫,我意识到在浪漫主义时期之前疾病是多么没有浪漫色彩。在这些早期作品中,疾病没有被当作一种精神状态或者末日天启,它们讨论的都是疾病应该如何被控制、管理和理智地对待。当我开始认真寻找,我发现直到18世纪中期之前都找不到任何关于疾病的隐喻的现代应用——这种观念将疾病当作人类身心状态的极端形式的一种形象化反映。
爱与性
要平静地去爱,毫不含糊地信任,毫无自嘲地去希望,勇敢地行动,以无穷的力量之源来承担艰巨的任务,是不简单的。
我认为性冲动具有无限的可塑性。人们一生中都会经历性欲的衰退和复苏。所以我认为人们无休止地追求的不是性,而是力量。回想一下有多少次性欲是通过展示力量的冲动来满足的,而且性有时候被当成一种文化上认可的方式,来对抗不安全、缺乏价值和吸引力的感觉。
自画像:作家眼中的自己
你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梦想,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要怎样做,或许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让它变得足够有价值。但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笔名从头再来。我会很喜欢那样做,卸下现有作品的包袱,一切重新来过,那太棒了。也许我会做一些不同的事……也许不会。或许我会拿自己开玩笑。或许我会用笔名发表作品……管它是什么作品呢,然后每个人都会大笑着说:“这绝对是苏珊·桑塔格写的!”因为我不会用别的方式写作,肯定很容易被认出来。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地前进再前进,到达新的起点,而不是回到原地。
在桑塔格的《意识听命于肉体:日记和随笔(1964—1980)》中,她在1978年8月20日的一篇日记中提出了一组“理想小说选”,包括罗伯特·瓦尔泽的《图恩的克莱斯特》、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月亮的距离》、劳拉·赖丁的《最后一堂地理课》和保罗·古德曼的《时光如暴风雪般飞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