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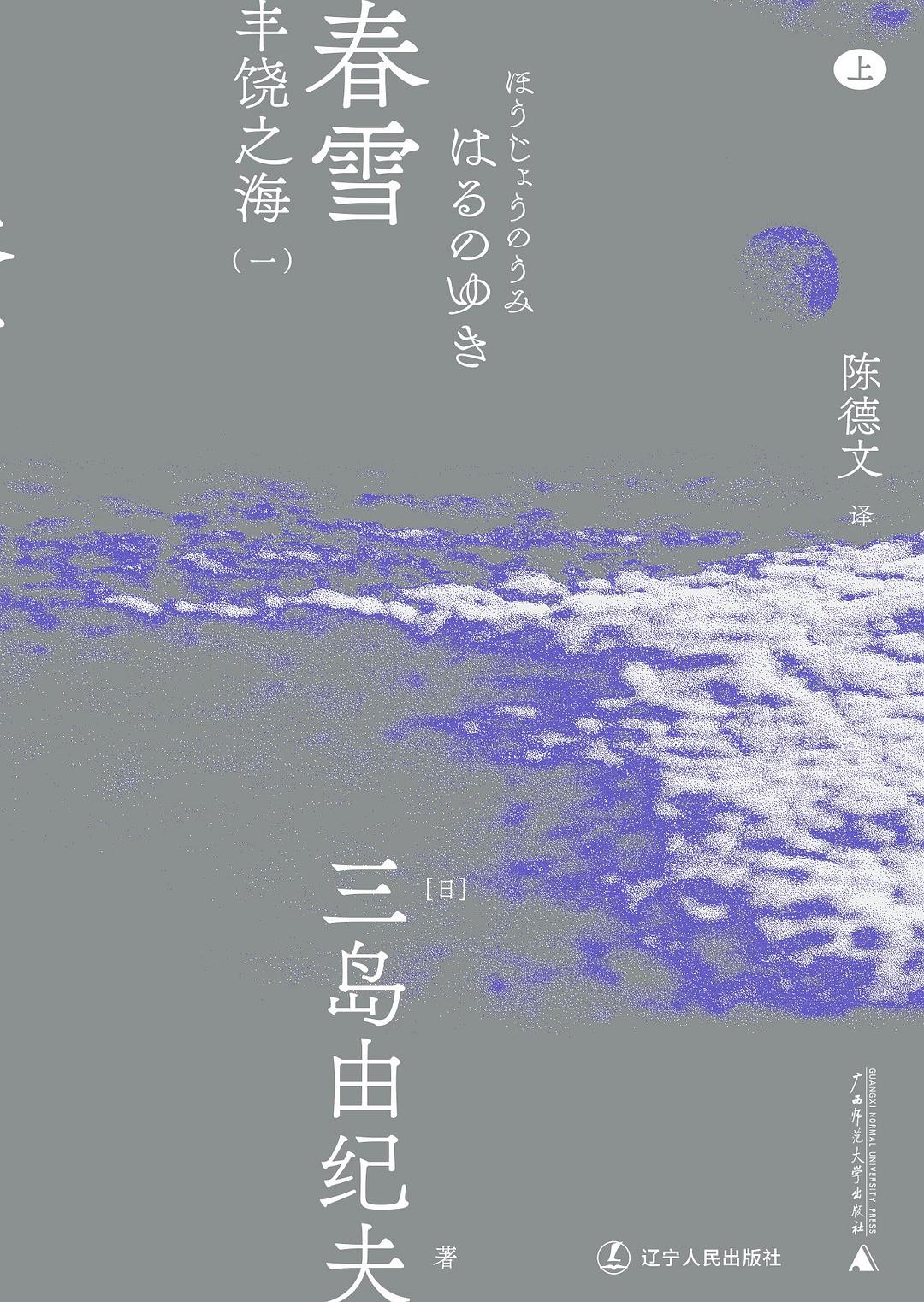
《春雪》三岛由纪夫
短评
不小心就迷失在整个文字构筑的精神迷宫中。三岛对男子美貌的描述登峰造极,对人生意义颇有一番见解又很极致,到挤得不能回头的死胡同去。
笔记
一
受到众人言语的触发,侯爵(清显父亲)从亲儿子的过分美艳之中,反而清醒地觉察出一种虚无缥缈的美貌。侯爵的心里产生了不安的征兆。
少年的身子埋在缎子被里,头靠在枕头上,直吐热气。从短短的发际到绯红的耳畔一带,皮肤特别薄嫩,似乎可以窥视到内部脆弱的玻璃体组织浮现着一道道鲜明的青筋。嘴唇薄暗而红润,从那里吐出的气息,听起来犹如一位不识苦恼之严酷的少年,偏偏又在戏说苦恼的歌声。修长的睫毛,不住闪动的细薄的水栖类的眼睑……饭沼瞧着这张面孔,他深知这位今晚完成光荣任务的盛气凌人的少年是不可指望他会有什么感激和忠诚的誓言的。
二
抑或清显和本多本是同根生的植物,各自长出了完全不同的花和叶。清显毫无防备地暴露着自己的资质,一副易于受伤的裸体含蕴着尚未足以左右本人行动动机的官能,宛若一只沐浴着初春雨水的小狗,眼睛和鼻子都沾满淋漓的水滴。同他相反,本多打从人生的第一步起,就觉察到世情险恶,他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将身子团缩于屋檐下,以便躲避过分明亮的雨水。
他是一根优雅的棘刺。而且,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那一颗忌讳粗杂、喜欢洗练的心,实际是徒劳的,犹如一株无根水草。他想蛀蚀,却蛀蚀不了,他想侵犯,也侵犯不得。这位美少年认为,他的毒刺对于全家来说固然有毒,但全然是无益之毒,这种无益可以说就是自己出生的意义。
他感到自己存在的理由是一种精妙的毒素,是同十八岁的倨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决心毕生不玷污自己美丽、白净的双手,不让它磨出一个水疱来。他像一面旗帜,只为风而生存。对于自己来说,唯一的真实就是单单为着一种“感情”而活着,这种“感情”漫无边际,毫无意义,死而复生,时衰时荣,既无方向,又无归结……
四
——清显一副任性的心灵具有一种奇怪的倾向,那就是使他不断增长自我腐蚀的不安。如果是一颗痴恋之心,如此的韧性与坚持,多么富于青春的活力!然而,他不是。比起美丽的花朵,他更爱扑向满是荆棘的黯淡的花种。聪子明明知道他这一点,所以才播下这粒种子的吧?清显为这粒种子浇水、育苗,最后整个身心都在期盼它枝叶繁茂,除此之外,他一概不予关心。他全神贯注培育着不安。
然而,他因此而悟出一条真理:心生则生种种法,心灭则与髑髅无异。
清显的眼眸此刻储存着一种切实而诚恳的愿望,甚至连本多也爱怜起来。这是祈望将一切都停止于暧昧而美丽的彼岸的眼神……在这种冷峻而近乎破裂的状态中,以友情做交易的无情的对峙,使得清显成为一个乞求者,而本多却成了审美的旁观者。这就是他俩暗自希望的状态,也是人们称之为两个人的友情的实质。
五
父母似乎谈得很有兴致的时候,清显总觉得他们是在举行某种仪式。他们的对话,仿佛是依次恭恭敬敬献给神佛的玉串,光洁的杨桐叶子也要经过一番品味才被选用。
母亲这时候当然不希望清显和父亲一起“散步”,父亲执意要拉着他的手外出。清显觉察到,父亲暗暗希望他背叛母亲。
六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所有神圣的东西,都是由梦幻、回想和与之相同的要素组成的,因时间和空间不同而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这些东西都是出现于我们眼前的奇迹。而且这三者的共同点都是不能用手触及。能够用手触及的东西,一旦离开我们一步,就会变成神圣的东西,变成奇迹,变成一种似乎不存在的美好的东西。一切事物皆具有神圣的要素,但因为我们手指的触及,随之变得污浊起来。我们人类是一种奇怪的存在。仅凭手指就能把东西弄脏,因为自己内心具有一种能够转化为神圣的素质。”
七
不,不仅是黑暗势力,本多还认识到,光明也会受到更加炫目的光明所胁迫,不断洁癖性地排斥较之自己更加光明的思想。包含黑暗的更为强烈的光明,还不是终于未被法制秩序的世界所吸纳吗?
西洋法的定言命令,永远服从人的理性,但《摩奴法典》将理性无法测知的宇宙法则——“轮回”,作为自然而然的道理深入浅出地提示出来了。
“行为产生于身体、语言和意义,也产生善或恶的结果。
“心于现世同肉体相关联,有善、中、恶之别。
“人以心之结果为心,语之结果为语,身体行为之结果受之为身体。
“人因身体行为之错误,来世变为树草;语之错误,变为鸟兽;心之错误生为低等阶级。
“对于一切生物保有语、意、身三重抑制,又能完全抑制爱欲、瞋恚的人,可获得成就亦即究极之解脱。”
“人必须正确运用自己的睿智,根据个人灵、法与非法规定自己的志趣,经常留意法的获得。”
八
清显喜欢马车。尤其是心中不安的时候,马车的晃动可以打乱不安独特的执拗刻板的节奏,而且又能贴近感受到赤裸的马屁股上甩动的马尾、高高耸立的鬣毛,以及咬牙时流下来的闪亮的泡沫和一丝丝唾液,再加上直接接触这种畜力的车内优雅的气氛,所有这些清显都很喜欢。
九
清显的美貌,他的优雅,他性格中的优柔寡断,缺乏朴素,放弃努力,充满幻想的心性,以及他那诱人的身姿,美妙的青春,还有那易伤的皮肤,梦一般修长的睫毛,都是对饭沼曾经有过的企图空前美好的背叛。他感到,这位年轻主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不断使他胆战心惊的嘲笑。这种挫折的愤恨,失败的创痛长久持续下去,会把人引入一种崇拜的感情。每逢有人对清显冷言冷语,饭沼就十分震怒,而且,凭着一种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合道理的直觉,去理解这位年轻主人无可救药的孤独。
十
饭沼被清显打败了,他感到这和被自己内部的肉欲打败完全相同,这使他甚觉奇怪。刚才一时的踌躇之后,他感到自己长久以来那种羞愧的快乐,立即和光明正大的忠实、诚信结合在一起了。这中间,必定有圈套,有诈术。但是,无地自容的羞愧与屈辱的底层,实实在在地开启着一方金灿灿的小门。
十二
这时候,清显的确懂得了忘我,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美貌。自己的美和聪子的美,从公平对等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的美无疑是像水银一般融合在一起了。他觉悟到,那些排拒的、焦灼的、尖刻的言行,其性质都和美毫无干系,对于所谓“孤绝的自我”的迷信,这种宿疾不存在于肉体,只寄生于精神。
清显用自己的指尖抚摸着她的耳朵、胸脯,他陶醉于一次又一次新鲜而柔软的触感之中。他学会了,这就是爱抚!他把即将飞离的雾霭般的官能一手揽住,化作有形之物了。而今,他只考虑自己的喜悦。这是他所能做到的最大的自我放弃。
十三
我要说的是,明治的模式正在走向死亡。然而,生活在模式里的人们,决不会看到这种模式,所以,我们也同样被包裹于一种模式里。这就像金鱼一样,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鱼缸之中。
“那么说什么可以作证呢?”
“时间,只有时间。时间的过程概括了你和我,将我们未曾觉察到的时代的共性,残酷地引证出来。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就会轻而易举地抓住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总体的真实。现在,就像一湾被搅动的水,平静下来之后,水面上忽然清晰地泛起一道油彩。是的,我们时代的真实,于僵死之后将被轻易地分离,让每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百年之后,人们就自然会弄明白,这种真实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我们也将被当作那个时代持有错误思想的人来统一对待。
“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后,历史也许很快就会采取同我全然没有关系的真正的梦幻、理想和意志的姿态,说不定这正是一百年前、两百年前我所梦想的形式呢,就像我的眼睛,带着一种任其想象的美,微笑着冷然地俯视着我,嘲笑我的意志一般。
“人们或许会说,这就是所谓历史。”
人的意志本质上可以说是‘企图关联历史的意志’。但我不是说,这就是‘关联历史的意志’。意志关联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仅是‘企图关联’。这同时又是一切意志所具有的宿命,虽然很明显,意志并不想承认一切宿命。
所以说嘛,西洋的意志哲学必须承认‘偶然’才能成立。所谓偶然,就是意志的最后避难所,一笔赌注的胜负……没有这个,西洋人就无法说明意志反复的挫折和失败。这种偶然,这笔赌注,我以为就是西洋的神的本质。意志哲学最后的避难所,如果是偶然之神,同时也只能是偶然之神,才能鼓舞人们的意志。
——不管怎样,我都一味想象着,看到必然之神的面孔,就只能感到恐怖和可憎。这肯定来自于我意志性格的软弱。然而,如果一次偶然也没有,意志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历史不过是一把隐含着因果规律的大锁上的铁锈,与历史有关的东西,只能起到唯一光辉的、永远不变的美丽粒子似的无意志的作用,人们存在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十四
清显希望饭沼能够亲手冒渎这块神圣的场所。细思之,清显打从美少年时代起,就靠这种力量,经常无言地威胁饭沼。这是冒渎的快乐。最好由饭沼亲自冒渎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这时的快乐犹如在敬神的洁白布帛上,缠上一块生肉一般。这是古代素盏呜尊喜欢冒犯的那种快乐……饭沼一旦屈服,清显的这种力量便会无限增大,但是使他难于理解的是,清显的快乐全部当成美好而清纯的快乐,而饭沼的快乐,越来越被看作是污浊的、带有犯罪的意味。一想到这些,他就越发把自己看得更卑贱了。
十六
墙壁横木上挂着一张模糊的照片,清显瞧着一身戎装的两位叔叔。他感到那军服和自己没有任何牵涉。虽然是一张八年前才结束的战争的照片,但自己和这照片的距离一派苍茫。他以一副略显不安而又颇为傲慢的心理思忖着:我也许生来只会流淌感情的鲜血,而决不会流淌肉体的鲜血吧。
二十三
一个想象力贫乏的主儿,往往直接从现实的事象中获取自己判断的食粮,而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会立即筑起想象的城堡,并把自己封闭于其中,关紧所有的门窗,清显也具有这种倾向。
他想到聪子的存在离自己一天比一天遥远,不久就要到伸手不可及的地方了,胸中涌动着难以形容的快感。好似看着布施亡灵的灯影照耀着水面,乘着夜潮渐渐远去,心里祈祷着漂得越远越好,越是远离越能证实自己的实力。
垂首而立的饭沼穿着深蓝色衣服,敞开的胸脯映着夕阳,微微显露出杂乱的胸毛。清显用一副沉郁的目光望着那里,饭沼的一颗富于威压性的忠诚之心,正是得到那堆厚重得令人心烦的肌肉的保护呢。他的肉体本身充满着对清显的责难,他那布满污秽粉刺的凹凸的面颊在闪亮,犹如洒在一片泥泞上的光照,辉耀着狂妄的余晖,向清显述说着,忠于自己的美祢也同他一道离开这个家。这是何等傲慢无礼!年轻的主子遭受女人的背叛,孤身一人;而学仆却获得女人的信任,趾高气扬,离开自己而去。
玉虫以这种光明绚丽的姿态一点点向清显靠近,这毫无意义的爬动似乎在向他垂训:时光在每一瞬间都无情地改换着现实的局面,他应该如何使自己每时每刻都活得光辉灿烂?他自己身上感情的铠甲怎么样呢?是否像这种甲虫的铠甲,散射着自然、美丽的光彩,并且具有抵御外界一切侵害的顽强力量呢?
二十四
他丧失了聪子,这很好。其间,满腔的愤怒也镇定下来。感情得到良好的节约,犹如一支为光明和热烈而点燃的蜡烛,身子化作蜡液而消融;一旦被风吹灭,峭立于黑暗之中,已经没有自身被销蚀的恐怖了。他懂了,孤独原是一种休息。
他认为,对自己来说只有一种真实,那就是单单为着既无方向又无归结的“感情”而活着……如果说这样的生存方式终于把他引入欢喜的黑暗的旋涡,那么最后只得葬身于深渊之中了。
二十七
毋庸置疑,他确确实实沉迷于甜爱之中了。清显挪动膝盖凑近聪子,双手搭在聪子的肩膀上,她的肩膀顽强地反抗着,他的手臂对她拒绝的感应令他陶醉。这种大规模的、祭典式的强有力的拒绝,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一样广大。这是带着君临于她那蕴含着肉欲的香肩上沉重“敕许”的反抗般的拒绝。只有这样的拒绝才能最有效地炙烤着他的双手、焚烧着他的心灵。聪子前额上蓬松的头发露着梳子清晰的齿痕,闪亮的黑发芳香四溢,那光亮一直到达发根。他朝她倏忽一瞥,似乎感到不小心误入了月夜的森林。
清显青春的活力立即苏醒过来,这会儿,他乘上了聪子平稳滑动的雪橇。当他随着女人的引导而前行的时候,他才初次体会到,不论怎样的难关都会畅通无阻,眼前风光旖旎。一阵燥热之余,清显已经褪去身上的衣服,他切实感到坚实的肉体宛若一艘采藻的小船,冲破激流与水草的阻力破浪前行。聪子的容颜不再泛起任何痛苦的暗影,面颊闪现出似有若无的喜悦之情,清显看在眼里,他并不觉得怪讶,心间的一切疑云顿时消隐了。
二十八
然而,行为的战争结束了,代之而来的,感情的战争时代到来了。这场无形的战争,那些头脑迟钝的家伙是完全感觉不到的,甚至不相信会有这种战争。但是,这种战争确实已经开始,为着这场战争所特选的青年们,无疑已经开始了战斗。你小子就是其中之一。
二十九
本多希望自己的理性永远成为那灿烂的光亮,但他难于舍弃为热烈的黑暗所吸引的心性。然而,这热烈的黑暗只是一种魅惑,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是确确实实的魅惑。清显也是魅惑。而且,这种从根本上摇撼生命的魅惑,实际并非属于生命,而是关联着命运。
三十二
本多一只手捧着沙子,倒腾到另一只手里,沙子漏光了,只剩下空空的掌心,他再次抓起一把沙子,但眼睛和心思全然被大海吸引住了。海就在这里完结了。如此广阔的大海,如此充满活力的大海,就在眼前完结了!不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说,没有比伫立于境界线上更加感到神秘的了。置身于大海和陆地如此壮大的分界线上,宛若站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一瞬之间见证了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移转,此时的心境难道不是如此吗?本多和清显生活着的现代,也不外乎相当于一次潮涨潮退时的境界罢了。
……大海就在眼前完结了。
他那白皙而柔美的体躯,只裹着一条红色三角裤,形成鲜明的对比,微微起伏的雪白的腹部和三角裤上缘相接之处,闪耀着干沙和贝壳细末的光亮。清显偶尔抬起左腕枕在头底下,本多发现他的左肋外侧,离开樱花蓓蕾般的乳头不远、平时被上臂遮盖的地方,集中生长着三颗小黑痣。
三十四
从那里可以径直走向深海般的喜悦,一心想融入黑暗的聪子,当她意识到这黑暗只是渔船的影子,不由一阵惶恐起来。这不是坚固的建筑物和山峦的阴影,只不过是很快就会进入大海的虚幻的阴影。船在陆地不是现实,这种看似固定的阴影亦似虚幻。聪子如今怀着恐惧,那只相当老朽的大渔船,眼看就要无声地滑下沙滩,逃进大海里了。为了追逐这只船影,永远待在那片阴影之中,自己必须变成大海。于是,聪子于浓重的充溢感之中,变成了大海。
三十五
“我清晰地看到闪闪发光的海水和沙滩,但我的眼睛为何没有洞察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微妙的质变呢?世界就像一坛葡萄酒在悄悄变质,而我的眼睛只是透过玻璃看到紫红的液体,我为何没有检验一下那酒味暗中微妙的变化呢?哪怕每天一次也好啊。我没有时时观察和谛听诸如早晨的清风、树林的颤动,还有鸟儿的飞翔和啼鸣,我只是把这些当成整个伟大生命的喜悦接受下来,而没有注意到世界一切美好的积淀,天天都在不住发生着彻底的质变!假如某一个早晨,我的舌头尝出了这个世界的味道发生微妙的变异……啊,假如有这么一天,我一定立即就会嗅出这个世界已经变成‘没有月光公主’的世界了!”
乔培说到这里,又哽咽着流下泪来,再也说不下去了。
三十七
面对这个比亲骨肉还要疼爱的姑娘,蓼科和聪子接触并没有感到自己怀着真正的悲哀。这种爱护和悲悯之间隔着一道栅栏,蓼科对聪子越是疼爱,就越是希望聪子和自己一起共享莫名的可怖的欢乐,那是隐藏在可怖的决断之后的欢乐!一种骇人听闻的罪愆,要通过所犯的别的罪愆获得救赎,到头来两罪相抵,二者均不复存在。一种黑暗,掺和进别一种黑暗,就会招来艳丽的曙光,而且都在隐秘之中!
蓼科觉得,她和聪子两个人一分一秒都亲密无间,不可分离。正如溯流而上的小船和河水的关系,两者力量平衡,小船就会暂时停在一个地方不动。同时,她俩互相理解共同的欢乐,这种欢乐,宛若逃离即将来袭的暴风雨而飞临头顶的群鸟搏击的羽音……这是有别于悲叹、惊恐和不安,只可冠以“欢乐”之名的粗犷的感情。
三十九
祖母显然满怀喜悦,紧绷的唇线松弛下来,长年的郁积获得了释放,到现在侯爵这一代凝聚于这座宅第的沉闷的空气,被她一下子扫荡尽净了。她为此而感到心满意足。这也不光是现任侯爵她儿子一人的过错。这座宅第周围有一股力量,十重二十重远远地围困着晚年的她,企图将她摧垮。祖母奋起反抗的声音,明显代表着已逝时代的音响。那个已经被现代的人所遗忘的动乱的时代,没有人害怕坐牢和处死,生活始终同死亡和牢狱毗邻,随处洋溢着一股血腥气。祖母的时代,至少属于那些若无其事蹲在死尸漂流的河边洗盘子刷碗的一群主妇。那才叫生活!这位乍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孙儿,能有这样的壮举,使那个时代的幻影重新在她眼前复活起来。祖母的脸上好一阵子神情恍惚,如痴如醉。
四十二
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看上去潮润润的,然而那种莹润似乎和清显所畏惧的泪水依然相距遥远。眼泪硬是被强忍住了。那是一位溺水之人径直向他投射过来的渴望救助的眼神啊!清显不由怯懦了。聪子修长俊美的睫毛,犹如一朵蓓蕾猝然绽开,向外部世界尽情展现着妍丽的鲜花!
四十四
聪子这才第一次正视着母亲,一双眸子摇曳着蜡烛小小的火焰,眼角里辉映着银白的曙光。夫人从未见过女儿眼中射出的可怖的曙光。聪子手里一颗颗佛珠也含蕴着一样的白色光亮。这一串意志达于极致而丧失意志的冰冷的佛珠,一起渗出黎明的曙色。
四十八
无为和悲哀对于以往的清显来说,本是头等亲密的生活元素。他总是乐此不疲、涵泳其中,然而,他是在何处失去这种能力的呢?就像稀里糊涂把雨伞忘在别人家里一般。
四十九
他的心中不断喷涌出不畏残忍而夸张的语言,仿佛对眼下自己的处境痛加鞭笞。而这些语言都是过去清显自己严格禁止使用的。
“一切都向我无情地袭来,我已经失掉陶醉的工具。如今,一种可怖的明晰统治着整个世界,这种可怖的明晰好似一弹指甲,整个天空就会引起纤细的玻璃般的共鸣……而且,寂寥是灼热的,犹如用嘴巴数度吹冷方可入口的沉淀的滚烫的汤汁,一直摆在我的面前。这只又厚又重的白色汤碗,带着棉被般的污浊与迟钝!是谁为我预订的这碗汤?
“我一个人被撂了下来。爱欲的饥渴。命运的诅咒。永无止境的精神的彷徨。茫然的心灵的祈愿……渺小的自我陶醉。渺小的自我辩护。渺小的自我欺瞒……失去的时光和失去的对旧物的依恋,火焰般燃烧着全身。年华空掷,青春虚度,岁月有闲,人生无果,为之愤恨不已……独自一人的房间。独自一人的每个夜晚……远离世界和人间的绝望的隔绝。……呐喊。谁也听不到的呐喊。表面的繁华……空漠的高贵……
“……这就是我!”
五十二
这般全然沉静的、每一角落都很明晰,而且含着莫名悲愁的纯洁的世界,其中心的内里,确确实实存在个聪子,她像一尊小小的金佛像屏住呼吸藏在这儿。然而,如此澄澈而生疏的世界,果真是她住惯了的“人世”吗?
他白净的手掌一点也不脏,没有磨出任何膙子。清显想到,他这一生始终爱护这双手,决不沾染泥土、血污和油汗。他的手只为着感情而使用。
五十三
煤油灯雾一般昏黄的光轮中,两个年轻人各自心里截然对峙的世界的影像,集中表现在那锐利的灯火的尖端。一个为刻骨的思恋而沉疴不起,一个为坚固的现实而勤奋学习。清显恍恍惚惚梦游于恋爱的海洋中,被海藻缠住双腿,依然挣扎着前进;本多幻想着要在地上建造一座坚不可摧、井然有序的理智的宫殿。一颗为热病所苦的年轻的头脑,同另一颗冰冷的年轻的头脑,于早春的寒夜,在这古旧旅馆的一角,紧紧靠在一起了。而且,各自都被迫准备迎接自己世界终局的时光的到来。
五十四
门迹跟他讲了因陀罗网的故事。因陀罗是印度的神仙,这位神仙一旦撒开网来,所有的人都逃脱不掉。一切生灵都牵连着因陀罗网而生存。所有的事物都是根据因缘果的理法而产生,这就叫缘起,因陀罗网就是一种缘起。
五十五
然而,他那疼痛得有些扭曲的容颜依然俊美,痛苦无形中给了他灵气,使得那张脸孔具有青铜般严谨的棱角。漂亮的双眼泪水盈盈,眼角向紧蹙的眉梢吊起,双眉攒聚,反而显得虎虎而有生气,眸子里平添了点滴黝黑的悲怆的光辉。端正的鼻翼不住翕动,仿佛要向空中捕捉着什么,因发烧而干燥的嘴唇里,灿烂的门齿散射出珍珠贝内部的光彩。
他怀疑,自己刚才看到的清显痛苦的表情,莫非是他在这个世界的终极见到了禁止观看的隐秘的欢乐之情?对于看到这一隐秘的朋友产生的嫉妒,沉浸在微妙的羞耻和自责之中。本多轻轻摇动着自己的脑袋,悲哀弄得他有些神志麻木,渐渐出现了一些连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的感情,犹如蚕丝萦绕心头。他为此而感到不安。
_________